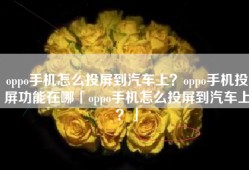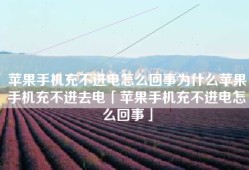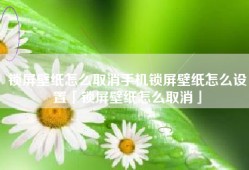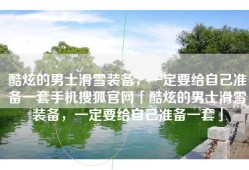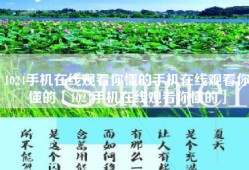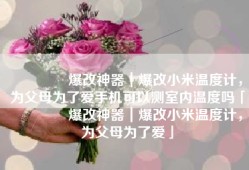芭蕉丨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香蕉手机网「芭蕉丨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
- 资讯
- 2025-03-05
- 68

江南园林造景,芭蕉必不可少。《红楼梦》里贾府营建省亲别墅,元妃将怡红院的题名由“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绿”便是那院中的数本(“红”是山石另一边的西府海棠)。探春说她最喜欢芭蕉,在诗社中雅号自称“蕉下客”。历史上也真有人痴迷芭蕉,宋初《清异录》记载,五代十国之一的南汉,皇帝身边有个亲信的太监“性惟喜芭蕉,凡轩窗馆宇咸种之”,时人称为“蕉迷”。古代的士人也多钟情于芭蕉,相关诗词不胜其数。芭蕉何以能如此受人喜爱?大夏天,正适合说一说。
1. 芭蕉与香蕉
芭蕉(Musa basjoo)是芭蕉科芭蕉属的多年生草本。对,它是“草”,不是“树”。看上去像茎的部分,其实是由叶鞘包裹而成,植物学术语叫“假茎”。[1] 这是芭蕉科植物共同的特点。芭蕉科植物约140种,主要产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们平常吃的(Musa nana),以及可供绿化观赏的、鹤望兰、地涌金莲、红焦等都是这一科的成员。
其中,芭蕉又和香蕉的关系更近,它们都是芭蕉 属,都拥有巨大的穗状花序。 见过芭蕉或者香蕉花序的人,一定会觉得以下北宋苏颂《本草图经》中的描述简洁又生动:
卷心中抽干作花。初生大萼,似倒垂菡萏,有十数层,层皆作瓣,渐大则花出瓣中,极繁盛。
相比于市面上的香蕉,芭蕉的果实要小,长5-7厘米,几乎无柄,果肉中藏有多枚黑色的种子,种子还有不规则棱角,因此不堪食用。
↑一种野生芭蕉属植物,种子很大 图自〔英〕威廉·罗克斯堡(William Roxburgh)《科罗曼德尔海岸植物图谱》(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
我们所吃的香蕉,一开始也如芭蕉一样含有种子。香蕉的主要亲本是小果野蕉(Musa acuminata)和野蕉(Musa balbisiana),它们的种子有黄豆一般大。
不过现代的香蕉,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人工选育的三倍体品种,它们可以结出果实,但很少产生种子,完美契合人类的需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香蕉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除了可以生吃的“水果蕉”之外,还有一种可以当做蔬菜或粮食的“主食蕉”。“这一类香蕉的株形较高大,但不耐寒。果实可作为蔬菜(适于炸、煮、炒、炖),替代马铃薯、薯蓣或其他淀粉食材。因为果实中的主要成分为淀粉,因此味道不是很甜。在法国和一些英语国家,人们也称之为‘大蕉(Plantain)’。”[2]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市面上卖的“芭蕉”,其实也是上述“大蕉(Plantain)”的品种之一,并不是我们庭院里种的芭蕉(Musa basjoo)结出来的。
经过漫长的自然杂交和驯化,出现了形态、口感多种多样的香蕉。下文提到“香蕉”时,泛指这些可食用的香蕉品种。
图自《本草图谱》
早在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已记载三种可以食用的香蕉,羊角焦、牛乳蕉、方焦。这些南方的物产,经不起霜冻,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才可以露天栽植。据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记载,甘肃天水不产芭蕉,有人从汉中移植了两棵,每到冬天则需连根掘起藏于地窟,待天气回暖再重新种于室外。有一年气温偏高,芭蕉突然开花,“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古时交通不发达,新鲜的香蕉不易保存,但“曝干可寄远,北土得之以为珍果”。(苏颂《本草图经》)。对于没有吃过香蕉的北方人来说,即便是晒干的香蕉片,也算得上是稀罕的食物。
我虽不是北方人,但第一次吃香蕉时,也应该觉得很美味吧。事实上那时我还没记事,听父亲说,有一对夫妇的多年顽疾被他的药方治愈(父亲曾在膏药厂工作),上门答谢时带了两挂金黄的香蕉,我和妹妹喜得不得了。回想起来,小时候吃到的香蕉真是香甜,似乎此后再也没能吃到那样可口的香蕉,有些时候甚至味同嚼蜡。也许是品种不同,或是摘得太早吧。
芭蕉的果实太像香蕉,所以每次见到都很遗憾不能吃。但芭蕉叶片用途不少,宽大的叶片在古代可代替纸张来练字。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就是在芭蕉上练字,他在住处附近种了几万株芭蕉,“取叶代纸而书”,并且将自己的居所也称作“绿天庵”。(北宋陶谷《清异录》卷上)芭蕉因此别名“绿天”。此外,芭蕉叶富含纤维,魏晋时人已用于织布 。[3]
↑在云南市场,芭蕉花和芭蕉叶都是摆在菜场里出售的食材
2.消夏与听雨
江南园林种芭蕉,可不是为了在芭蕉叶上练字或拿去织布,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美化装饰。对于文人雅士来说,芭蕉是庭院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植物,是其闲情逸趣的一个重要部分。
魏晋时王子猷爱竹,到别人家暂住也要种下竹子,称“何可一日无此君”。清代李渔认为,芭蕉和竹子一样“能韵人而免于俗”,而且比竹更易于存活,“蕉之易栽,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图画,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因此“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闲情偶寄·种植部》)
李渔对于芭蕉的欣赏主要在于审美的层面:令人免俗,坐于其下即成风景。但古人种芭蕉还有非常实际的功用,那就是在炎炎夏日消暑纳凉。这一方面归于它带来的一片树荫,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全身皆绿,就像李渔所说能将周围的环境都染上碧绿清幽的颜色。窗前如有一株芭蕉,就仿佛有凉风习习。正如明代王守仁《书庭蕉》所言:“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
↑元 刘贯道 消夏图(局部) 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因此,在古代一些表现消夏主题的画作中,时常可见一丛碧绿的芭蕉,例如元代画家刘贯道《消夏图》,画中主人公(“竹林七贤”之阮咸)的卧榻后边即是两株。清代黄图珌梳理高人逸士额的生活情趣,以下关于芭蕉纳凉的描述,可以作为这幅画的最佳注解:
蕉绿窗前,极为凉爽。当盛夏时,科头赤足,高卧其下,觉清气自生,炎威顿解。(《看山阁闲笔》卷十三“芳香部·赏花”)[4]
纳凉还算比较务实,但下面这个用途绝对称得上风雅:听雨。在下雨时聆听雨点打在芭蕉上的声音,这恐怕是古人种芭蕉更重要的目的。芭蕉的叶片大,下雨时雨水打在上面噼里啪啦,声音之清脆响亮,非其他植物可比。就像南宋王十朋《芭蕉》所说的:“草木一般雨,芭蕉声独多。”
所以在古典诗词中,芭蕉与雨是一组经典搭配,就像梧桐和雨一样。不过雨滴多表达离愁别绪;雨打芭蕉则不同,更多的是表现闲暇时的悠然自得,而且这雨最好是夜雨,因为能伴着这雨进入梦乡。例如杜牧《芭蕉》:“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怜渠点滴声,留得归乡梦。”再如北宋贺铸《题芭蕉叶》“隔窗赖有芭蕉叶,未负潇湘夜雨声”,南宋杨万里《芭蕉雨》“芭蕉得雨便欣然,终夜作声清更妍”,因为有芭蕉,一场夜雨也变得浪漫起来。
但这种“欣然”也只有在处于闲适的状态下才能体会。对于正在遭遇人生变故的人来说,雨里听芭蕉,只能平添烦忧,例如李清照《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下阙:“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但是这不能怪芭蕉,所以南宋方岳《芭蕉》说:“自是愁人愁不消,非干雨里听芭蕉。”
了解芭蕉听雨的文化内涵后,就能读懂陆游晚年蛰居山阴时所写的这首《忆昔》。诗人在回顾平生“淋漓纵酒”“慷慨狂歌”的英豪岁月之后,嗟叹“壮士有心悲老大,穷人无路共功名”,最后自我安慰“生涯自笑惟诗在,旋种芭蕉听雨声”。种芭蕉、听雨声,看似洒脱自在、怡然自得,实则饱含年华已逝、壮志难酬的悲情和无奈。
虽然芭蕉雨不似梧桐雨一定指向负面的情绪,但新生未展的芭蕉叶,却多指代未能打开的心结、未能抒展忧愁。 著名的例如李商隐《代赠》: “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这首诗写情侣二人无法相见。 一个在高楼上望眼欲穿,一个被玉梯阻隔而无法登楼; 一个如同尚未展开的芭蕉新叶,一个是含苞未开的丁香花蕾,都因为相思无法相见而各自忧愁。
比李商隐稍晚,唐末诗人钱珝[xǔ]则以“未展芭蕉”为题,用来比作芳心未展的少女:“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冷烛、绿蜡、一缄书札,都是对“未展芭蕉”的比喻;“犹卷”的不仅是芭蕉的芳心,也是少女未能吐露的芳心。“未展芭蕉”也成为诗词中的一个常用意象。
说到此,再回 到开头的《红楼梦》,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袋囊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元妃请宝玉和妹妹们为“怡红院”等园子赋诗。 宝玉为“怡红院”所作“春犹卷”一句被宝钗看见,宝钗赶忙提醒宝玉将“绿玉”换成“蜡绿”:
宝钗转眼瞥见,便趁众人不理论,推他道:“贵人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才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又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分驰了?况且蕉叶之典故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罢。”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拭汗说道:“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
宝玉因问“绿蜡”可有出处,宝钗的回答就是上面钱珝的那首诗。这可让宝玉深感佩服:“从此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又被宝钗笑道:“还不快作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
宝钗的情商和学养,以及对宝玉的护爱,都通过这段由芭蕉用典产生的小插曲展现了出来。
[1] “一般茎所具有的表皮、皮层,形成的层、髓等结构它都没有,所以我们把这段‘茎’称作假茎。”“芭蕉也是有茎的植物,不过它的茎生长很慢,而且节间很短,在一株生长多年的老芭蕉的基部,就可以看到真正的茎。每年从茎的中心生出新叶,然后慢慢地从假茎中心抽出并展开它的新叶。”见:马炜梁、寿海洋著《植物的“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19页。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已认识到这个特点,说芭蕉之类的植物是“草类”,“其茎虚软如芋,皆重皮相裹”(《本草纲目》卷十五)。
[2] 〔葡〕若泽·爱德华多·门德斯·费朗著,时征译《改变人类历史的植物》,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0页
[3] 《齐民要素》卷十“芭蕉”引《异物志》:“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濩而煮之,则如丝,可纺绩,女工以为絺[chī]绤[xì],今则‘交阯葛’也。”
[4] “科头”指不戴帽子。“高卧”即高枕而安适无忧地躺卧,也多指隐居不仕,如《晋书·隐逸传·陶潜》:“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作者简介:江汉汤汤,企业职员/ 中国美术馆志愿者讲解员 /植物文化普及者,著有《古典植物园》(商务印书馆,2021.4)。个人微信公众号【古典植物园】。
摄影、图文编辑:蒋某人
本作品采用 (CC BY-NC-ND 4.0) 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deed.zh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xinmeigg88@163.com
本文链接:http://www.xrbh.cn/tnews/100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