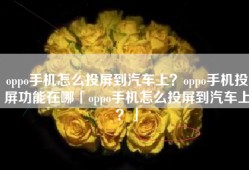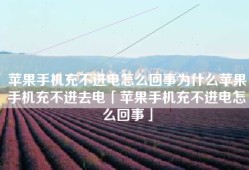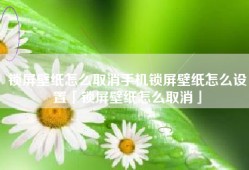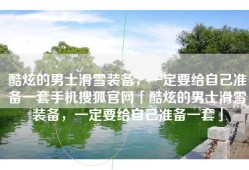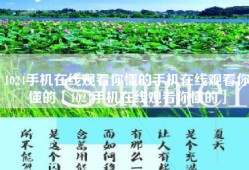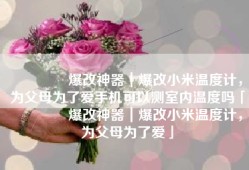为什么《芭比》是一部保守的大型商业广告电影
- 资讯
- 2025-04-20
- 80

第一部分:从芭比到女性
在大众文化当中,芭比一直以来都被作为物化女性的代表,其根基是一种对年轻女孩的幻想的兜售:对于奢华梦幻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女性身体图像的想象,而这一根基则是芭比这一品牌能成功的根本要素。而在电影《芭比》之中,在主创格雷塔的改造之下,芭比摇身一变,成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不再甘愿作为一个居住在塑料城堡里的玩偶,而是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独立女性。而我们可以对本片的玩偶做进一步隐喻的衍生,玩偶代表着女性被客体化,被物化,对自己的生活姿态与选择没有掌控的一种被动状态,而对玩偶状态的打破,去成为一个不完美但真实自主的女性,这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解放性与颠覆性的女性主义表达。
但当我们跳脱出《芭比》试图游说的叙事逻辑之外再去对其进行审视时,我们就能发现其所展现的打破玩偶与被客体化物化的女性状态的,那种颠覆性的女性主义姿态是完全不成立的。
而原因可以粗暴地用一句话总结:《芭比》是由美泰公司出品的一部好莱坞电影。而此片应该达成的最大功能是对美泰旗下芭比品牌进行重塑,以对扩大其文化影响力以及市场的销售量,而作为制片人的玛格罗比也深知这一点,这也是她借此来说服美泰与华纳公司的负责人的。因此,无论《芭比》想采取多么激进的姿态,它到底都不可能去动摇其所根基于的品牌以及产品本身,而美泰旗下的芭比说到底仍然要保留其产品的核心,即作为一个玩偶以及其作为玩偶引申出的对于女性形象的客体化与物化。
BRITTNEY MCNAMARA所撰写的文章《Study Shws Barbie Dolls Negatively Impact Young Girls’ Body Image》,对芭比娃娃对年轻女孩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女学生萨沙在影片中曾精确地指出了现实当中对于芭比这一形象的分析与批判,认为其给予了女性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滞缓了女性主义的运动,但在这之后无论是芭比中的角色们还是芭比的主创似乎都没有任何兴趣再去探讨这个极为重要也是核心的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着的。因而这个批判也就变成了一种犬儒主义式的批判:我知道我这样是错的,但我对它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批判,现在我们就可以继续以这种错误的方式享乐了;而影片在最后让经典芭比打破了其作为玩偶的限制,不再被芭比这个品牌所定义,而来到现实成为一个真实的女性,这看似是一个激进以及具有解放性的设计,但真正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如果经典芭比选择的道路是具有解放性,那与其反之的那种生活,那群仍然生活在塑料城堡里的芭比为何不能同样获得解放,仍然要作为以及被认为是陈旧腐朽的芭比世界的一部分呢?而如果经典芭比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那其他的芭比现在又是什么呢?
而这些尖锐的问题本片是永远无法回答的,因为其是必然要保证其品牌的根基的:即芭比要向其受众兜售关于梦幻生活与女性身体图像的幻想。而由于其对于现实的资本与市场逻辑的必然遵守,我们就得到了与其所宣传的女性主义观念截然相反的,影片内与外的双重保守。在《芭比》的故事内部,这种保守以一种改良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影片的结局,芭比在与美泰创始人罗莎的和解,以及美泰现任ceo的良心发现之下发生了所谓”颠覆性“的改变,这则造成了一种影片传达内涵中的虚伪与自相矛盾:我们要反对父权制,但是要保留那个管理我们,给予我们经济支柱,给我们分一杯羹的那个父权制(美泰公司就是一例证,甚至可以说它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实体,不断地稳固其自身的统治),而我们要靠其良心发现与充满善的感化,让其带领整个体制变得更好。
芭比与其创造者罗莎·汉德勒
而芭比CEO在最后承认道一个基于现实的有瑕疵的女性形象的芭比甚至会更为卖钱,以一种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自指涉了芭比也是本片在现实中的一个位置,芭比与《芭比》都仍然处于资本逻辑之中,是华纳影业下,美泰公司出品的品牌宣传电影,而这个看似更为进步解放的芭比与《芭比》只是美泰旗下的最新款商品,而其受众也不再仅仅天真充满幻想的女孩,还包含了期望着一种女性主义抗争的满足的独立女性群体。在电影《芭比》之外的各种联名奢侈品牌,芭比娃娃的再度热潮以及流行文化中“粉红热”的掀起正印证了美泰这一全新版本的芭比带来的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第二部分:从芭比世界到现实世界
在《芭比》中,影片致敬了《黑客帝国》中一个经典“红蓝药丸”的瞬间,是沉浸于享乐,留在幻想之中,还是面对真相,进入现实。在本片中很明显的,其幻想与现实的对立对应着芭比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对立。但是影片中的这一对立的两者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泾渭分明,《芭比》一片在此犯了两个错误。
《芭比》的红蓝药丸瞬间
首先,影片对于代表幻想的“芭比世界”是不以为真的,但是实际上芭比世界这一虚构世界是有其现实性的,借用《创世纪》中的那句名言”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男男女女”,那么男男女女按照自己的(想象性的)形象创造了芭比。如上一部分所说,芭比世界里的构造与人物到底仍然是遵循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以及父权制逻辑下的框架创造出来的,这是这一品牌能够迎合市场,数十载来影响力逐级递增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正是芭比对于这些逻辑的遵循以及影片对其幻想的架构与故事中的现实性的忽视,导致了其所展现出来的影片内外的双重保守。
而与芭比世界相对的真实世界,影片则是对于其是过于信以为真的。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芭比》中所呈现的那个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其是完全扭曲的。在《芭比》中选取的现实的代表竟然是位于加州,那个全球最大的梦工厂好莱坞所在的地方,名流明星科技大头娱乐中心汇集之地,一个与芭比世界大同小异的“现实”,或者说是一个现实的“芭比世界”。而当影片将此作为现实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想到《黑客帝国》中的对于现实揭示的那一幕,当尼尔逃离虚拟世界,从现实中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于密密匝匝,巨大的母体之中,所有人都向其汲取能量为食。这难道不是对于加州以及其中的好莱坞的完美隐喻吗,加州可以说就是母体所制造的幻想与景观的中心,而母体便是其背后的金融业,文化产业,电子业以及好莱坞电影工业等一众的资本主义的景观生产机器,在其中充斥一个个罗丝·韩德勒,夜以继日地生产着一个又一个类似于芭比世界的为世人所梦寐以求的幻想与景观:真人秀,好莱坞电影,名车,名模,别墅,给予其中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源源不断赖以维生的能量:幻想与娱乐。
《黑客帝国》中的母体
《芭比》中幻想与现实的交界线
因此当芭比从芭比世界来到现实世界时,这并不是从幻想到现实的巨大跨越,而是从一个兜售幻想的景观到一个更大的兜售幻想的景观,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电影《芭比》也便是这巨大景观中的一个产物,这一点同样也在影片的叙事层面中体现出来,其中所展现的那个”现实”就如同母体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幻想,去遮掩现实中的创伤与残酷。
在影片中象征着真实的凉拖鞋也讽刺地在现实中成为了芭比联名的时尚商品
首先,本片试图去对女性主义进行讨论,但是却对于影片中为数不多的现实的女性角色葛洛丽亚,对于其背景以及角色心路历程的挖掘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葛洛丽亚作为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上被压迫位置的女性,同时也是毫无疑问受到父权制下传统性别观念压迫的女性,其现实的创伤与痛苦并未在影片中得到任何具体的展现,最终只沦落为推动第三幕故事发展的剧情工具,而由于对葛洛丽亚的心路历程与现实经历的挖掘与发展,最后的独白只显得空喊口号,只为引发女性观众的共鸣的迎合之嫌。而葛洛丽亚这个角色也应该给芭比从玩偶到女人的转变提供现实的根基与教训,但毫无疑问影片在这一点上也是失败的。
葛洛丽亚的独白
其次,出于要与其芭比世界幻想与卡通化的故事基调的一致性,影片对于“现实”的男权主义压迫也是夸张化与过于危险的“简单化的”。在芭比第一次来到“现实世界”时,影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展现了每一个遇见芭比的男人都会对其进行性骚扰,而路边“游手好闲”的工人更甚,如连环炮似地来了一段“性骚扰贯口”。而对于美泰公司的高管们,对于芭比的命运掌握生杀大权的男权主义者们却又卡通化般的愚蠢可笑。也许是出于本片商业电影的身份,也许是出于创作者本人的立场,在此影片很明显没有意图想要对于现实的父权制的统治与压迫结构进行严肃探讨,一方面将男权主义的压迫的根本原因归于观念上的压迫以及底层的(无产以及中产)男性民众(这些男权主义者毫无疑问的是压迫者,但绝对非是生产与稳固父权制的最根本与底层原因),一方面又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主义者二元化(一会是愚蠢但邪恶的,一会又是天真而真诚的),并未意识到父权制的根本来源以及能够不断再生产的原因正在于这些资产阶级男权主义者对于政治,教育,文化,经济生产领域的掌控与运作。
第三部分:从“芭比”到“芭比世界”
当芭比进入现实,成为其一部分时,这可看作是整个景观兜售的那种幻想的实现,从玩偶到一个女人,再变成一个典型的加州的资产阶级成功女性形象,由此再反过来去维持芭比玩偶的那种文化产品生产与幻想的兜售。而芭比与“现实世界”所构成的那个更大的景观也以同样的方式如法炮制相同的幻想的循环: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观的生产,不断地给消费者兜售幻想,生产出类似于芭比这样的文化产品与景观,到受到其影响的年轻女性,在其消费主义文化产品的诱导下产生对于女性身体图式的幻想,以及资产阶级化,从而最终进行资本主义景观的生产机制当中,而对于资产阶级化失败的女性,她们现实的创伤与不平则由这个循环当中源源不断的兜售幻想的文化与娱乐产品抹平与抚慰。
由此整个循环构成了如《黑客帝国》中的母体,源源不断地构造着我们所处的“现实”,生产着一个又一个的芭比与芭比世界。当人们诧异于那些由于对于芭比形象所呈现的幻想过于表面性的理解的那些人,不惜对自己进行一次次的塑形手术来使自己变得更像芭比,我们应该更担忧那些真正理解芭比的想象性图式下的隐喻意义,而有条不紊地按照其想象图式去塑造自己生活的那些人,也许我们对此过于习以为常了。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xinmeigg88@163.com
本文链接:http://www.xrbh.cn/tnews/11440.html